深度访谈丨重生·共生音乐会:这四部新作缘起何处?
- PNWCEC
- Jun 13, 2023
- 9 min read
作者:洲际听觉 2023-03-31

2023年6月25日下午7点,重生·共生——黄晓枫博士交响作品世界巡演首站将在美国西雅图 Benaroya Hall 贝纳罗亚音乐厅拉开序幕!

本期,洲际听觉将对话作曲家黄晓枫博士、本场演出的指挥家之一涂东钶先生,深入探寻创作背后的时代与环境背景,共同探讨这场音乐会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我小时候跟随父母在三线企业,三线企业当时是都是在农村。因为企业不能都在大城市,为了防止战争破坏,就分散一部分企业建在偏远的农村,所以我也跟着一直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当时我们那个三线企业的家属房跟农民就隔了一条街,前面就是生产队的农村居民。所以我们那个学校也都是跟当地的农民孩子在一起的,因为企业占了本属于农民的土地,所以作为交换,他们的孩子就近到我们企业的子弟学校上学,就不用再跑到远处他们的公社学校去上学了。
我十几岁时,恰逢文革时代,大抵有一整年的休课。夏季我成天跟前街的那户农村小孩一同去生产队放牛。他跟我年龄相仿,每天上午骑着牛到山上去,然后把牛放开自己吃草,我们就自己进山嬉戏,采摘野果,摸鸟蛋,冬天就一同去山里劈柴。后来我经历了一次非常震撼的终生难忘的旅行,是到我大伯家。他家是在长白山脉的深山老林里。一个生产队只有十几户人家,只能是马车过去,没有电,也不通汽车。我在那里待了整个寒假、过了年。那时我真正了目睹长白山的深山幽林,当时是冬天,所到之处是成片铺展的桦树林,漫山遍野的白雪皑皑,毫无生气的枯叶落木,直到我突然见到一棵光秃秃的树上生长着一簇生机盎然的冬青,孱弱却又硬朗,你可以感觉到大地的某些难以言喻的本质,这对我后来的音乐创作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在严寒或荒芜的景观中,给每一个新的音符赋予原始的生命,或脆弱,或诡谲,或坚韧,有时有些肖斯塔科维奇式的共振。
尤其是我下乡的时候,农村三年,更亲切于土地、农民和整个大自然。我们是一个文艺集体户,二十多个青年,这期间除了农忙时候就是在排练演出。下乡加上中学时期的三年,一共有六年的时间几乎是全部在排练演出,那段时间深度接触了各式各样的民族曲艺、舞蹈和音乐,并渐渐在我的音乐观里生根发芽。我最初接触到交响乐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县里来了一个京剧团演出现代京剧《红灯记》,他们有一个乐团现场伴奏。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西方器乐。但往后的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些,试着一个个声部听写下来,然后再搬上自己的舞台来演。

七十年代念中学和下乡这六年,我几乎是全职排练演出,接触了大量的广泛的中国民族音乐。而在美国通过和孩子共同练琴、一场不落的当地乐团排练、电台的古典音乐频道、专业的作曲修习,西方音乐就是这样自然而然、润物无声地在我脑海中弥漫、开花结果。
在慢慢把中国和西方音乐逻辑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我也渐渐察觉工程领域的诸多思想方法和当代音乐实践的许多共通之处,比如音乐中的音色或声色 (Klangfarben) 构造与工程学中运用的有限元法之间的联系。我的小提琴协奏曲的引子段落,让小提琴的四根空弦音 G, D, A, E 在各个声部间做矩阵变换,这就包含着工程学、后调性理论以及当代哲学思想给我的灵感。

我想从我个人的经历出发,通俗地谈一下这个问题。我自己的经历让我意识到,要求一个人既创作当代音乐,又要有民族性的传承,是两难的要求。如果说要有传承,你就必须对中国民族音乐有深层次的洞察力,而不是浮于表面。人一辈子也就几十年,没有太多精力左顾右盼。交响乐即使在西方也不是完全大众通俗的,而对中国来讲更是在象牙塔尖上的舶来品,整个社会大环境也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古典音乐的气氛,只有在音乐学院和各大音乐团体里面才可能稍稍有那种氛围。所以,如果你不在音乐大院那个圈里,你要考作曲专业几乎是很难的。但是,当你的创作需要那种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动感时,你又需要具备一些真切的、扎根的生活阅历,这无疑只能在学院的圈子之外,甚至需要在大城市之外的乡镇或村落才能体会。所以,在中国能培育交响乐作曲的那个西方式氛围的圈子和能培养对中国民间音乐有深刻经验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两极世界。
所以我或许是比较幸运的。我在中国小时候六年时间接触民族音乐,那个时候正是人的一生中最好的学习时段。中学时代接着又下乡三年,是精力最旺盛的阶段,是记忆力最强的年纪,在此时非常自然地接触到各种中国音乐,但囿于彼时条件有限,我只能把收音机里听到的音乐一个个声部“听写”成谱。然后上大学学工,出国留学,获得工程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美国的前六年里忙着研究生学业,听当地乐团的每一场排练和演出,每周一次,期间自己温习了小提琴和钢琴,后又跟随作曲家Roger Briggs先生学习作曲11年。所以我的经历有点阴差阳错,在乡下时期对中国的民间音乐有了深切认知,然后留学美国,又在西方音乐文化中浸润了二三十余年。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理想化的过程。通常你很难有这样美丽的、天然融合的音乐经历的,因为大多数人几乎不可能在不同的领域之间跳跃自如的。
我认为创作音乐首先需要“能听”,我说的这种可听性不是满足一小部分人的听觉趣味,而是对不同文化下大部分观众的可听性,然后再才需要一些的新的音乐洞见。无论从我个人的经历还是我们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情来看,人民要素和人民性是未来音乐使命不可或缺的部分。我觉得这也是我对自己音乐创作的要求。作曲家需要超脱琐碎,对大地、人文和哲学命题具备一定的敏感度,另外从华人作曲家的角度,我们还要讲华人的音乐传承。但是,以何传承?何以传承?何以真正传承?这些是每个作曲家都需要深思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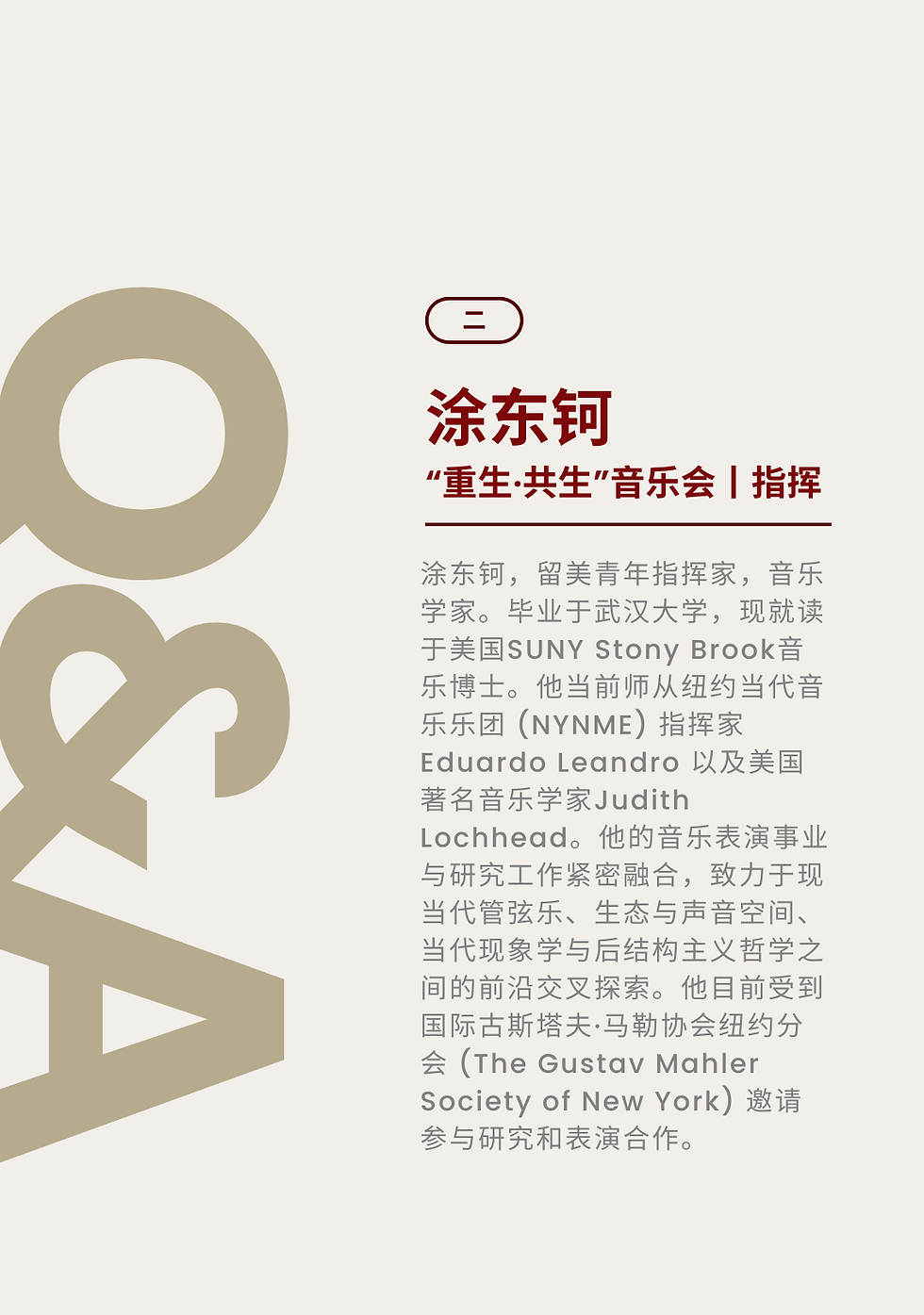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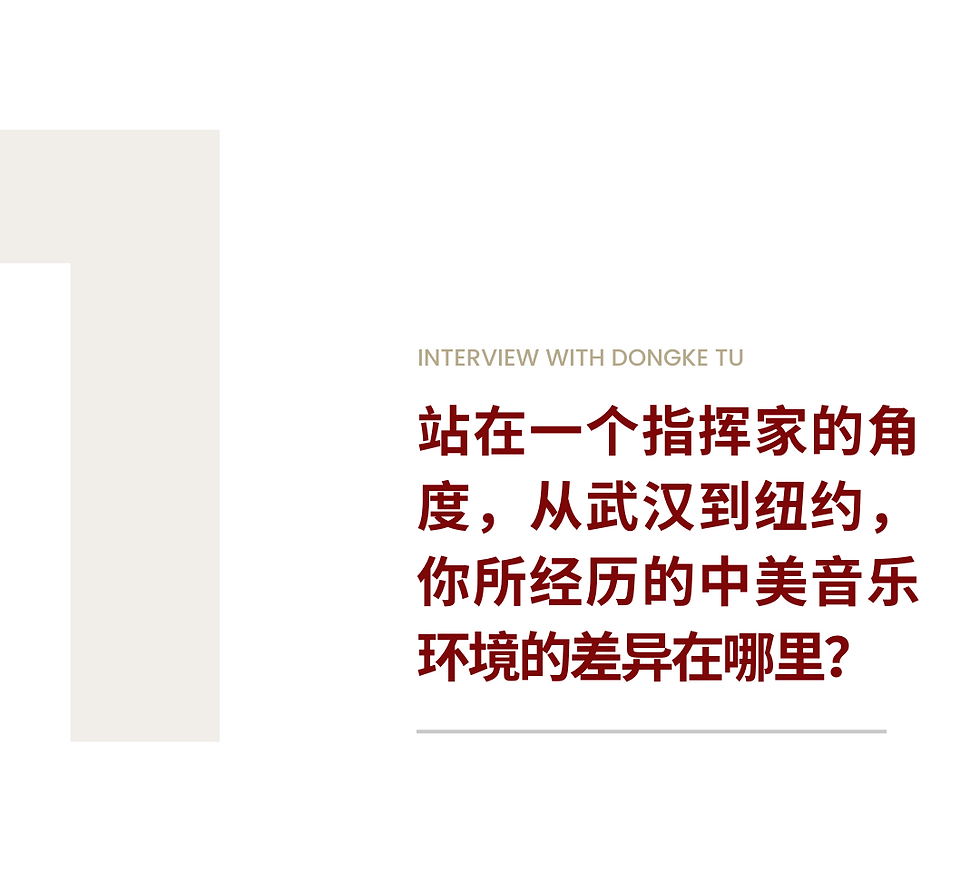
指挥是音乐中一门引导声音信息与能量进行交互的艺术。我生长在武汉,迄今也邂逅过世界上各色各样的音乐厅和乐队,但我感受到中国音乐最难能可贵、无以替代的景观是源自于市井生活的声音生态——吆喝声、车铃声、方言、戏腔、地下演奏会、街头艺人、民间小调和民族音乐,它们共同塑造着任何“学院”都无法替代的一种“亚音乐”(quasi-music) 氛围,一种原初性的、流动的、棱角未平的声音-生存状态。这种亚音乐氛围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我在指挥时身体张弛运动的逻辑,以及我在指挥特定作品时声音能量交流中瞬息万变的角色。而美国音乐圈看上去多元化的音乐氛围,主要源自于对形色各异的音乐价值、方法和文化的平均包容(与其说“包容”,不如说是一种中庸、妥协和默许),无论是传统音乐院系那些程序化的、工具理性至上的运作方式,还是新型音乐院系新旧势力的嬗变更迭,抑或是美国本土强势的民间音乐或非古典音乐话语,它们之间似乎各自达成了一种防守型的静默。你可以在自己坚信的音乐价值和道路上做到顶尖,而所有路径本身却是性质均等的、默认合理的,有点积分理论中“路径无关性”的那种味道。多元主义 (pluralism) 是诱人的,但时而也是危险的。
许多进步性的新一代学者和音乐家们(包括我自己在内)似乎都有过一种自相矛盾的经验,就是你能在宏观上感受到一种无处不在的论说、创作或表演自由,但在许多琐碎的地方却几乎处处受限。而音乐活动在中国和美国的实际上有着不同层面的琐碎限制——前者更出于宏观制度,后者更出于微观制度。但无论是面对调控式的组织逻辑,或是面对晦涩繁冗的技术逻辑,那些面向音乐本身的真诚而真切的话语、实践、疑难乃至必要的纷争,都在程序与工作理性至上的艺术体制中被平均化,或是渐渐分散掉了。以美国为典型,当代音乐话语中的这种“毫无疑难”的状态,便是我们新一代进步性音乐家们最需要去面对的最大疑难。艺术家自身就是世界使命的一个矛盾体——我们需要去创造一些裂隙,又需要去缝合一些裂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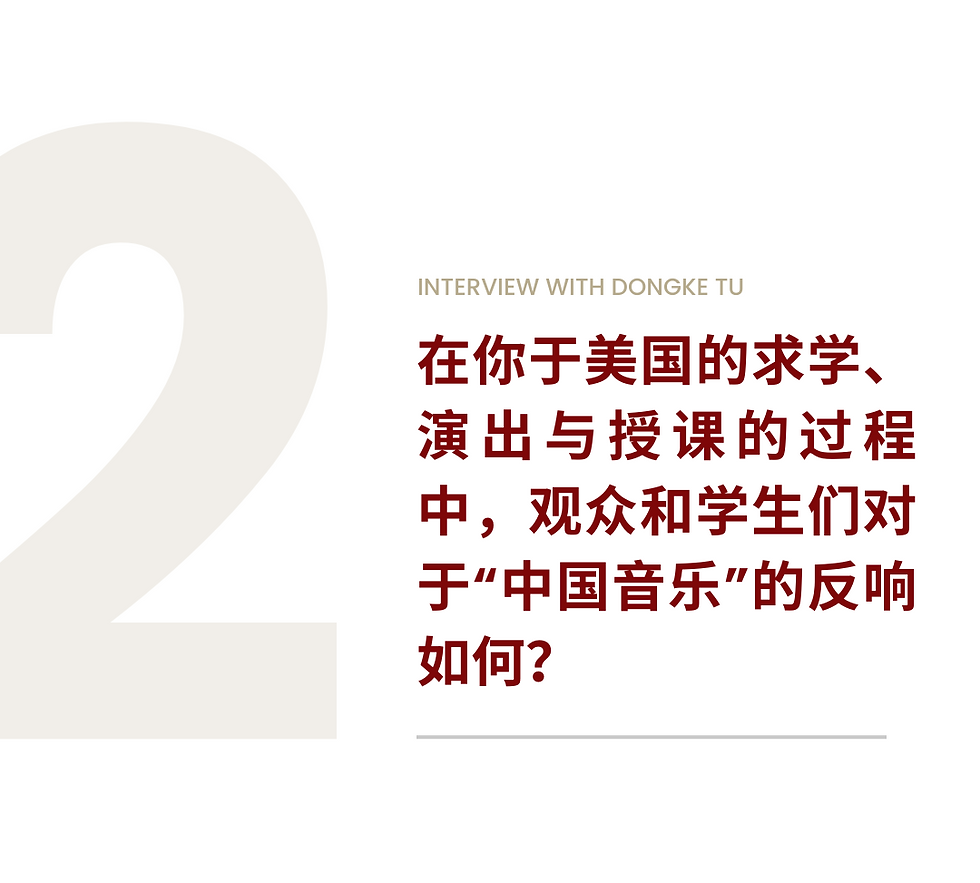
我所接触到的许多美国本土的传统爱乐人士,他们对于含有中国音乐、甚至整个东方音乐元素的管弦乐作品大多都比较欢迎和赞赏。但他们对这些音乐的赞赏和他们对贝多芬、舒伯特或者布里顿、斯托克豪森等西方作曲家的赞赏是不同维度的。使他们为之激动的是,非西方音乐的逻辑拓宽了他们对管弦乐语汇和意义的认知边界,让他们在“相同”的乐器编制下深感“不同”。然而,这样的音乐(甚至是整个严肃音乐文化,无论东西方)目前对在美国的华人学生群体是不太有吸引力的。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我教过的学生覆盖各色各样的国籍、身份和种族,但总体来讲,我接触到的许多华人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意识确实稍显茫然,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状。

我认为教育和话语壁垒是最大的阻力。一方面,赴美华人以从事理工或商管类为主,经济效益和计算性效益是他们的首要考量,除非是这些领域中专门的爱乐人士,否则很难同相隔甚远、又冗长而抽象的严肃音乐产生情绪或思绪上的关联。而另一方面,美国人文学科的“博雅教育”却充斥着许多不加思索的、饱含逻辑缺漏的新潮观念,留下一个形式主义的人文躯壳,标新且激进,热切而无头绪,博雅而无纵深,新奇而罔现实;而音乐学院内部艰涩的技术系统、速成式的排练、无差别的表演机制、纠缠不休的学分和竞赛体系又加固着这道无形的围墙,观众群体则渐渐成为音乐活动中被遗忘的大多数。当“形式性的人文”逐步取代着“沉思性的人文”,当一种人类学式的、精英主义的无差别创作、表演和研究成为霄壤之别的世界音乐文化的传声筒,那么民族音乐最基本的表达和传播能力也将渐渐丧失。
作为华人音乐家的一份子,我认为我们最需要克服的是一种浩大的漠然,一种海德格尔所说的“丰富的空洞性”。我很欣赏希腊指挥家库伦齐兹 (Teodor Currentzis) 前期的“地下音乐”实践。其实新音乐和当代音乐并不站在古典音乐的对立面,反倒是我们在坚守古典音乐的道路上,往往需要来自一些土质的、现实的、大地的、人民性的要素,而不是类宗教式的技术壁垒和竞赛崇拜。我从库伦齐兹身上察觉到一些伯恩斯坦式的影子,他把19世纪末甚至20世纪才使用的铜管力度处理运用在贝多芬后期的交响曲中,而无视所有那些莫须有的制度压力、话语壁垒甚至是“时空错乱”的指控。在音乐的“实存现实”(actual real) 之外,探寻“潜存现实”(virtual real) 的种种可能。作为晚辈指挥家,我应当更坚定地继承这种艺术胆识。

我和作曲家黄晓枫先生本人进行过许多密切和深入的交谈,无论是从个性还是从音乐性格上都对彼此相当了解和欣赏。与其他同辈作曲家比起来,黄先生的个性无疑是独特的:刚与柔的协和,豁达与深邃的并济,亲和与决断的共存……尽可形容,尽相对照。同样,我认为他的音乐对中美观众都将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新而不浮,大而不躁。他并不屈从于学院派的艰涩冰冷的无调性写作,也从未陷于传统音乐结构和规则的繁文缛节。
在民间与自然景观失落于主流管弦乐文化近半个多世纪之后,黄晓枫正试图把它们重新带回到当代管弦乐的视域中。秦腔、劳动号子、铜钦、西雅图的油渍摇滚、七十年代的中国老调……他们被移出人类学式的“声音博物馆”的展架,向生存而复苏,回归流变。我见过把《心经》写进交响乐规模的情形,但从未见过像这样让一个深不可测的六声音阶游走在极繁和极简“之间”的禅宗景观,把“此有”到“万有”的现象学要义展开在音乐场景与生存场景之间的相互引力中。实际上,并不是说这四部作品体现了某些“思想”或者“意义”所以它才“新”,而是反过来,是观念自身的流动造成声音景观的生成和更迭。如果说“某音乐体现某观念”的陈词滥调成为当代教科书般的解释定式,那么黄先生的作品则是让“观念驱动音乐”远远走在“音乐体现观念”之前。
原文发表于:https://mp.weixin.qq.com/s/QxaYGk59c_-ST4I6H2o2KA



Comments